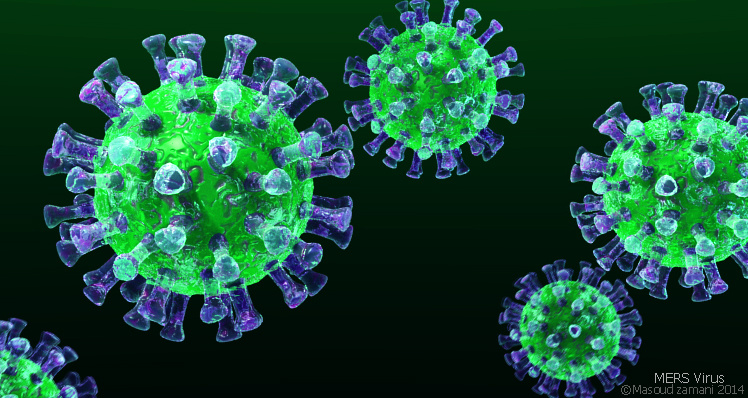一摩尔原子有多少?阿伏伽德罗常数又更新了!
文章来自果壳网;北京方程佰金转发一摩尔的原子有多少个?在教科书上,答案通常是6.02x1023,这个数字也就是阿伏伽德罗常数。这个近似值足以应付化学习题,但它还远远不够精确。那么,精确一点的阿伏伽德罗常数应该是多少呢?《物理与化学参考数据期刊》(Journal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Reference Data)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给出了最新的答案:6.02214082(11)x1023(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最后两位估值数字的不确定性,确切地说,阿伏伽德罗常数还要加上单位mol-1)。在此前,研究团队已经对阿伏伽德罗常数进行了若干次的测算。他们采取的测量方法是计数1千克重的高纯硅-28球体中有多少个原子。当硅结晶时,它会形成规律的晶格结构,每个基本的晶胞中含有8个硅原子。如果能分别得知硅晶体总的体积,以及每一个硅原子所占的体积,就可以计算出其中硅原子的数量,而这可以通过对晶格参数(lattice parameter)的测量实现。在今年的早些时候,研究团队测得了新的阿伏伽德罗常数,测量的误差控制在每十亿个原子相差20个原子以内,与2011年的测量结果相比更加精确。最终,综合多次测算结果,研究团队得出了上述阿伏伽德罗常数的最新数值。测量阿伏伽德罗常数所使用的硅晶体球。图片来自:Eurekalert更精确的阿伏伽德罗常数有什么用?一个重要的用途是赋予“千克”这个质量单位更加精确的定义。一千克质量的标准来自一个铂铱合金的“标准”圆柱体,但无论性质多么稳定,千克原器的质量实际上也不能保持恒久不变,因此计量学界希望可以用物理常数替代实物来重新对千克进行定义。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研究之后,千克将会在2018年通过普朗克常量正式进行重新定义(更多阅读:新型原子钟有望重新定义“千克”单位)。在那之前,科学家们需要首先保证普朗克常量的数值足够精确,而测算阿伏伽德罗常数是间接为普朗克常数“校准”的一种方式。虽然阿伏伽德罗常数并没有正式成为定义质量单位的标准,但计数这些硅原子依然可以帮助人们检查基于普朗克常数的新标准是否足够准确。(编辑:窗敲雨)
新品
2015.09.01
氰化钠究竟有多危险?
文章来自果壳网;北京方程佰金转发(文/三畝)提起氰化钠,很多人都会闻之色变。甚至有媒体以“核生化部队爆炸现场测出钠元素,钠遇水易爆燃”为题进行了报道。不过实际上氰化钠中的“钠离子”不危险,危险的是这次爆炸现场可能存在的“氰化钠”这个物质中的另外一半——“氰离子”,而更危险的是不做任何调查直接把听到的东西变成新闻的不求甚解的态度。“氰”是不是彻头彻尾的坏?我们先别着急下结论。首先“氰”有一个挺美好的名字。这种离子和青色的东西有点儿关系,所以西方人管她叫做Cyanide“青色”在英文中是“Cyan”),非常有名的染料普鲁士蓝(Prussian blue)就是一种含有“氰”的物质。实际上,普鲁士蓝是一种救命的药物:对于铊中毒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普鲁士蓝。图片来源:dailytech.com普鲁士蓝里面的“氰”之所以能够安安分分地做不产生毒性,是因为在普鲁士蓝里面还含有一些居委会大妈——“铁离子”。“铁离子”能够牢牢地把“氰”抓在自己身边不让他们出去捣乱。可是如果是“氰化钠”就不行了。这个组合里面的“钠离子”搞不定“氰”。如果这个“氰化钠”没有溶解到水里面,那么这个“氰”还算是老实,能守在“钠离子”旁边不跑。但是只要空气里面有一点点湿气,“氰”就会见缝插针地随着这点儿湿气跑出去,同时形成一个叫做“氰化氢”的剧毒气体。这种“氰化氢”略微带着一点儿苦杏仁味,所以你看动画片中的柯南经常会闻闻死者的嘴巴,然后只见一道闪电从脑海中劈过:真相只有一个,死者氰化物毒死的。《名侦探柯南》中,受害者死于氰化物中毒的情节。图片来源:b.bbi.com.tw当然要是遇到更多的水(比如南方梅雨季节里面能拧出水来的空气或者干脆就是一杯水),“氰化钠”里面的那些“氰”就会更加撒欢儿往外跑。“氰”跑出来会干嘛呢?如果在动物(包括人)体内,这些“氰”就会牢牢地抓住身体里面的“铁离子”大妈:“我可算找着您了,‘钠离子’太不给力了,还是您带着我吧,您带着我吧。”这要是在别处也就算了,“铁”大妈带着就带着。可是动物体内的“铁离子”太重要了,人家要运送比“氰”重要一千倍的东西——氧;运送氧还是次要的,还有更多的铁离子在细胞内运输重要一万倍的东西——呼吸作用所需的电子流。这是维持细胞运作最根本的动力。一旦“铁”大妈被“氰”给缠住了分不开身,它作为电子传递链的正常任务就无法执行了,细胞呼吸由此断绝,能量的供应也都断掉了;而一旦能量缺失,控制身体所有机能的中枢神经系统就会极快停止工作。接下来,呼吸和心跳就会停止,各大重要脏器(比如肝和肾)就会衰竭。很短时间内生命停摆。普鲁士蓝毒性很小,因为在普鲁士蓝里面人家“氰”已经找着组织“铁离子”了)。“氰化钠”、“氰化钾”和“氰化氢”剧毒(根据法医学经验,氰化钾的致死量在50毫克到250毫克,也就是0.05克到0.25克之间)是因为这些物质里面的“氰”都还是活动能力很强的,没被看住。到底有多毒呢?用我们经常用的LD50(lethal dose 50%,在指定时间内杀死测试动物中一半数量所需要的剂量)指标对比,砒霜是(大鼠口服)14.6毫克/千克(体重),而氰化钠是(大鼠口服)6.44毫克/千克(体重),氰化钾是(大鼠口服)5毫克-10毫克/千克(体重)。也就是说,这东西比砒霜还要厉害三分。更可怕的是这些剧毒的氰化物很容易在水里溶解的,所以起效非常快(我们的黑话叫做“动力学速度很快”),除非剂量非常小,15分钟到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置人于死地,给医生留下的抢救时间非常有限。相比较而言,砒霜可以算是慢性子了,服毒1小时后开始看到症状,几个小时甚至一天之后才会致死。见血封喉是啥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顺便说一下,这两天有个谣言说小心不要淋雨,因为雨里面可能有这个东西。嗯,这么说吧,如果您要是淋到的雨里面的这东西浓度高到能够透过皮肤造成伤害的话,您也就没有机会站着淋雨了:空气里面的氰化氢的含量已经把您给撂倒了。氰化钠的工业用途既然这个“氰化钠”这么厉害,而且这东西遇到水就会变成别的东西,那么一定是有坏蛋把这匹猛虎给放出来了!这是个阴谋吗?是有人制造出大量氰化钠来害人的吗?还真不是这样。氰化物最主要的用途是在金和银的开采上。由于“氰”这个傍大款的脾气,他见到“铁”大妈的时候就牢牢地抓住“铁”大妈,见到“金”大妈和“银”大妈的时候当然就更加揪住不放了。在冶金行业中,就是利用“氰”的这个见钱眼开的脾气来把矿石中稀稀落落存在那点儿“金”和“银”给抠出来。开采金矿使用的氰化钠。图片来源:globalchemmade.com除了这个,氰化物还用来做橡胶,还在制药行业中有用处。所以不能冤枉别人,这东西只要管理好了还是挺有用处的。那到底该怎么管理呢?要想让这些家伙始终做个“安静的美男子”,就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密封容器之中,搁在阴凉并且通风良好的地方。不要让他们有机会和水见面,尤其不能见到一丁点儿酸(醋都不行,不要说盐酸硫酸硝酸这样的东西)。以前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氰化钠是放在一个密封的小瓶子里面,小瓶子外面就是专门中和氰化钠毒性的“硫代硫酸钠”(另外一个居委会大妈,大概相当于朝阳群众,专灭“氰”这种捣蛋脾气)。这样就算遇到什么不可控制的情况(比如地震),氰化钠这小子跑出来了也立刻被干掉。当然,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需要人的观念上的改变。再良好的规范,如果大家都不能够按照规范操作的话,就都白搭了。(编辑:球藻怪)本文首发自微信公众号“言安堂”,经作者授权转载。言安堂微信号:Yan_Huang_TH。
百态
2015.08.31
玻尿酸是保湿圣品吗?
玻尿酸(Hyaluronan,或Hyaluronic acid)还叫透明质酸时,还没这么有名气,改名叫玻尿酸后,突然就火了。透明质酸是一种高级多糖,由D-葡萄醛酸及N-乙酰葡糖胺组成,并且不含硫(这一点使它与别的粘多糖区别开来)。因为它有较强的携水能力,所以受到美容界的重用。玻尿酸保湿真不错其实玻尿酸是皮肤中天然存在的填充物,起着保湿、修复、营养皮肤的作用。保湿是皮肤护理的重要一环。我们的皮肤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表皮和真皮。真皮如同慕斯蛋糕下面海绵状的蛋糕,而表皮就是覆盖在最上面的一层奶油。真皮在表皮下面,主要成分是各种纤维以及纤维之间的基质。基质可以结合大量水分,是真皮组织保持水分的重要物质基础。透明质酸就是真皮中含量最多的基质之一,若真皮基质中的透明质酸减少,会导致含水量下降,进而导致皮肤干燥、无光泽、弹性降低、皱纹等。表皮是皮肤最外层的保护屏障,正常情况下其含水量为20%-35%。当表皮的含水量降低到10%,就会发生明显的皮肤干燥:无光泽、细纹、粗糙以及脱屑等,而且自己也能感觉到皮肤不舒适、瘙痒等。这时,就要请作为保湿剂的透明质酸出场了。在环境湿度相对较低时,外用透明质酸可以从环境中吸收水分“锁定”在表皮上;同时,少部分渗透入真皮的透明质酸,可以从真皮中吸收水分并传输到表皮,达到“由内而外”的保湿效果。与其他常见的保湿剂,譬如丙二醇、甘油、尿素等相比,玻尿酸的保湿功效略胜一筹,且多数玻尿酸制剂无油腻感,用后能即刻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薄膜,使皮肤变得光滑和滋润,因此被广泛用于各类化妆品。但是含玻尿酸的化妆品的价格“相当昂贵”(与甘油、尿素1-2元的价格相比),所以从各种保湿剂的性价比来说,玻尿酸并不一定是最优选择。保湿,一个好汉三个帮虽然透明质酸的保湿作用优于同类,但是,只用玻尿酸来保湿是不够的。这是因为,保湿并不是简单地将水分吸收到皮肤中去,真正的保湿需要保留住皮肤中的水分,尽可能阻止或延缓水分经表皮流失,同时让表皮纹理变得光滑。因此,一个完美的保湿计划除了要有保湿剂,还要有封闭剂和润肤剂。玻尿酸会在角质层(或是皮肤表面)形成一层富含水分的薄膜,同时向内(皮肤)、向外(环境)输送水分 。因此,环境干燥时,还要依靠封闭剂减少它向外的水分蒸发,才能持久保湿。封闭剂可以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薄膜,阻止水分“跑路”,通常都比较油腻,例如凡士林、矿物油、硅树脂衍生物等。润肤剂则是填充表皮最外层细胞间的空隙,使皮肤表面纹理光滑、柔软,在短时间内体现化妆品的功效和美容效果。根据不同的内在特性,又可以分为保护性的、去脂性的、干性的或收敛性的。玻尿酸除了保湿以外,也有一点润肤剂的功能。事实上,现在市场上口碑较好的保湿产品往往是三者的“混合物”,特定配方往往用于特定皮肤类型,调节水油比例。因此,购买护肤品时,需要首选了解自己的肤质,然后寻找适合自己的配方和剂型才行!注射见效快,效果难维持外用的护肤品需要“仰仗”表皮的渗透能力和吸收作用才能进入真皮甚至皮下发挥作用。但如何才能让护肤品有效成分很好地穿透表皮屏障,一直让研究人员头痛不已。不得不说,目前尚无很好的方法能仅通过涂抹就让透明质酸进入“深层”。现有的较成熟的将玻尿酸导入真皮或皮下组织的方法就是“注射美容”,也就是通过很细的针头将透明质酸导入真皮或皮下组织,不同的导入量还有不同的临床作用。注射量少时,可以用于填充皮肤的细小皱纹或疤痕,让皮肤恢复平整和弹性。注射量多时,可以用于重塑局部的外观,例如提高鼻梁、修复鼻尖、丰满脸颊、丰满双唇、修复唇形、修饰下巴等等。虽然临床上使用玻尿酸是做填充之用,但我个人接诊过的病人们都表示,注射玻尿酸后,附带有些保湿的效果,皮肤也变得细腻有光泽。一方面可能是增加真皮或皮下组织中玻尿酸含量,可能增加了向表皮传输的水分,但更有可能是注射玻尿酸对于真皮的刺激增加了胶元蛋白的合成,才让皮肤变得细腻有光泽。(编辑吐槽:难道没有可能仅仅是因为注射了玻尿酸把表皮给“撑开了”,显得细腻有光泽吗?)由于玻尿酸是身体本身就有的成分,因此只要是在正规医疗机构使用合格的产品,注射玻尿酸还是比较安全的,而且效果立竿见影。不过,玻尿酸的缺点就是人体会对它进行吸收,所以要维持效果,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打针。文章来自果壳网;方程佰金转发
百态
2015.08.21
诺奖夫妇发现“速度细胞”
信息来自果壳网,北京方程佰金转发(远千山/译)走路,跳跃,奔跑……人们能以各种不同的速度运动。只是,我们的大脑是怎么区分不同速度的呢?用GPS导航时,系统会根据你的移动速度调整周围的地图。在动物的大脑里,是否也有发挥着“速度计”的机制?图片来源:shutterstock友情提供要拼全“大脑GPS”,可能就差“速度计”这一块拼图近日,挪威的研究者们发现了大鼠大脑中的一组可以作为“速度计”的神经元。它们可以记录动物运动的速度。这些“速度细胞”不断更新脑内的地图,帮助动物对周围环境进行定向。研究论文被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研究者们已经知道大脑是如何处理位置、方向、距离和边界信息的了,而速度细胞则是大脑地图领域最后一块重要的拼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吉姆·尼里姆(Jim Knierim)说到。他并没有参与这一项目。2014年,约翰·奥基夫和莫泽夫妇因为发现大脑"GPS"的重要成分而获得诺贝尔奖。图片来源:nobelprize.org 编译:果壳网在发现“速度细胞”之前,人们曾经发现了网格细胞。通过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奥基夫(John O’Keefe)、爱德华·莫泽(Edvard Moser)和迈-布里特·莫泽(May-Britt Moser),我们了解到网格细胞能帮助描绘动物的运动。当许多网格细胞共同协作时,它们就构建起了大脑地图的坐标系统——经度和纬度线。网格细胞的基本任务是确定大鼠的位置,但它们也会给出关于速度的信息。“然而,在这一领域里,还没有人发现特异性编码运动速度的细胞。”尼里姆评论道。找到“速度细胞”的,还是莫泽夫妇为了寻找速度计神经元,爱德华·莫泽和他的同事们为大鼠设计了类似《摩登原始人》中那样的车子。这种装置没有底部,所以当车子前进时,大鼠的爪子会踩过地面。研究者会控制这辆“大鼠车”运动的速度。如果车子移动的太慢,大鼠会悠闲地走动。当速度增大时,大鼠会撒足狂奔。这辆车或者磨磨蹭蹭,或者疾驰而过,以不同速度多次穿过同一段跑道。研究者则会记录每一次旅程中大鼠的大脑嗅皮层活动。他们发现,大脑嗅皮层中15%的神经元会特异性地对大鼠的速度做出反应。如果大鼠加速运动,这些神经元会发放得更剧烈。但如果大鼠慢下来,这些细胞的活动也会减弱。当大鼠在宽敞的空间里自由移动时,速度细胞同样也会有反应。发放的程度取决于大鼠运动得有多快相关,而和大鼠的位置无关。迈-布里特·莫泽和一只受试大鼠。图片来源:Kavli Institute/NTNU快速发放,提前准备速度细胞似乎也具备一定的“先见之明”。爱德华·莫泽说,它们会“提前60-80毫秒就设定好速度”。换句话说,它们似乎会在大鼠加速之前就开始行动,在实际需要到来前一点点(就配合网格细胞)帮大鼠预先建立起认知地图。在一个神经元传递一条信息后,它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恢复并传递一条新信息。然而,有些神经元恢复的速度比其他更快。研究中大约四分之一的速度细胞都属于“快速发放”型,这就意味着它们需要的恢复时间更短并且而更容易发放。了解这些速度细胞的特点,将会帮助研究者们建立计算机算法来模拟我们在空间中的运动方式。如果将小车换成过山车,莫泽和克里姆都表示速度细胞仍会有反应,但应答会与在原实验中不同。换成过山车后,跑动的部分就不需考虑了,计算速度的部分由我们的其他感官参与。当大鼠开始运动时,这些感觉——肌肉怎样变化,风如何吹过皮毛,以及眼前的景象怎么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速度细胞的反应。研究者猜测,人类也会有大脑地图,但对其中所涉及的神经元,我们了解得更少。莫泽的研究团队将进一步研究不同感官是如何影响到速度细胞的。他表示,虚拟环境中的实验也许可以帮上忙。科学家们可以检测一只静止的大鼠看到它周围环境在屏幕上飞速变化时,它的速度细胞会如何反应。或者,他们也可以记录虚拟环境保持不变而大鼠奔跑时,速度细胞的发放方式。(编辑:Calo)文章题图:shutterstock友情提供
新品
2015.08.04
MERS会是全球性威胁吗
文章信息来自果壳网;北京方程佰金转发(Paradoxian/译)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在中东外最大一次爆发引起了世界的持续关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的6月8日的数据,韩国现已有50人感染,其中4人已死亡。(编者注:6月9日,据中新网援引韩联社报道,韩国MERS确诊患者的增至95例,死亡病例增至7例。)几百所学校已停课。引发此轮爆发的冠状病毒MERS-CoV被认为是诸多潜在流行病威胁之一。然而,《自然》新闻发表的一篇文章称,专家们并不认为此次全部与医院相关的MERS爆发会引发大流行,原因如下:MERS-CoV并不是人类病毒;MERS-CoV主要在医院中传播;韩国目前做得很好;MERS并不是“非典”;此次爆发规模并不大。MERS-CoV并非人类病毒一个病毒若要引发大流行病,必须得能在人类间轻易传播。但MERS-CoV却不行——这种2012年在沙特阿拉伯首次发现的病毒本来是动物病毒。该病毒被认为起源于蝙蝠,出于偶然通过中介动物——有可能是骆驼——才传播给了人类。正如在韩国正发生的那样,这个病毒偶尔能在人类间传播。但此类案例只在医院,或者在家中照料感染者(这种情况少得多)时有过密切接触的情况下发生。此次爆发始于一位5月4日从中东四国旅游归来的68岁韩国人。在被确诊前,他将病毒传给了医护人员、家属,以及他接受过治疗的四家医疗机构里的病人。若要造成MERS大流行,MERS-CoV需要突变到能在人际更广更轻易地传播——但流行病学数据表明,此次在韩国的爆发并无异常。MERS主要在医院传播虽然MERS-CoV并不是人类病毒,但在一个地方——医院里,它有时表现得挺像人类病毒的。在医院,医护人员对未确诊病人所采取的医疗措施,比如呼吸辅助等,可能会从肺部产生气溶胶,污染那片区域并使附近的人员感染病毒。其它情况下,由于MERS-CoV通常感染在肺部深处,通常并不会被咳出。在这次爆发中,传染源在5月11日出现了咳嗽和流感样的症状,但他直到20号才被确诊。这造成了一个没有特殊防护措施的空窗期,这也解释了病毒是如何自他传开的。他在确诊前分别在4家医疗机构接受了治疗,这又给感染他人增加了更多风险。韩国做得很好因为MERS-CoV在人类间不容易传染,MERS疫情能通过公共卫生措施加以控制——韩国当局也在积极地开展这样的工作。韩国当局在追踪并监视感染者的接触者方面做得非常严密,凡接触者都会被监视14天——这是该疾病最长的潜伏时间。任何开始出现相关症状者都会被隔离。目前为止,所有新增病例都出现在已被记录在案的接触者中,这让人们更相信此次爆发正在受控。尽管每天都有新的案例报告出来,但它们并不意味着病毒有了新一轮扩散,因为这些人全都出现在韩国第一例MERS-CoV感染者在确诊前所接触过的1600人里。导致MERS的冠状病毒还没有演化至能在人类间轻易传播。图片来源:Scinceside/commons.wikimedia.orgMERS不是SARS在过去的一周里,有些人可能会联想到2003年扫荡全球的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但就算猛烈如SARS,最终也被控制住了。况且,它和MERS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导致SARS的冠状病毒已经演化出在人际轻易传染的能力。相比之下,MERS-CoV则没有。它有没有可能演化出像SARS-CoV 般的能力,然后造成非典那样的爆发?病毒是不可预料的,所以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但这也并不是无法避免的。在这样的爆发中,人们会例行对病毒进行测序,检测任何遗传变化。不过,考虑到目前在韩国并没有出现传播模式的异常,我们还没有必要提到这种假想中的演化。当前爆发规模并不大此次MERS爆发可能是在中东之外最大一次,但在规模上并不特别。2014年春天,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Jeddah)发生的一次爆发致使255人被感染,而2013年位于沙特东部哈萨(Al-Hasa)一家医院的集体感染事件,则造成了23人确诊,11人疑似感染。沙特还发生过十几次发生在其他医院的爆发,这促使当地的卫生机构对医院工作人员进行感染防控。而此次韩国的爆发中,被感染的人数也可能有所虚高——当局对接触者进行了全面的病毒筛查,因此可能包括了一些以往医院爆发中没检查出来的温和案例。(编辑:Calo)文章题图:Scinceside/commons.wikimedia.org
百态
2015.07.30
协助科研方案设计与SCI相关服务!
方程佰金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可开展以下服务:科研文献论著翻译 SCI论文翻译、编辑、协助发表 临床实验/科研实验设计方案指导对于发布文章,我们有如下优势:主要修改专家曾在PNAS(IF>10)等杂志上发表过数十篇文章,具有丰富的SCI论文写作和发表经验,帮他人修改的诸多论文均成功发表于SCI刊源的学术期刊。修改专家由中英文造诣深厚的资深留美研究人员和英语为母语的美籍人士共同组成,特别对Chinglish及其它亚洲语种作者的英文有独到的理解与修改能力,确保科技英文的准确和纯正。从科学和语言两方面为您的论文双重把关,对口修改农业、生物、医学等大生物类论文,保障对您的论文内容完全把握。独具特色的数据图表美化服务,是您的数据图表更直观地呈现;独有的反驳信润色,亦是基于多年经验的特色服务。因语言问题造成发表失败100%退款——是我们信心的体现,也是对您的高度负责。严格的保密政策。保护您的知识产权和隐私。
商机
2015.07.28
代做生物实验(实验外包项目)
北京方程佰金科技有限公司与国内多所高校科院所构合作构建多个实验平台,目前可开展绝大多数种类生物实验项目,目前与我们合作的有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细胞,分子生物学,免疫,病理,MicoRNA实时定量PCR检测Western-blot 实验服务EMSA实验技术服务引物设计合成、基因测序激光共聚焦细胞原代、传代培养 细胞模型构建、转染蛋白双向电泳实验服务ELISA(酶联免疫吸附法)技术服务等
商机
2015.07.28
DNA也是可以改变的吗
信息来自果壳网;方程佰金转发合理运动的好处不胜枚举,它既能燃烧多余的热量,令人们的身材更加健美,也可降低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等诸多疾病的风险,但这一系列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依旧是一个未解之谜。 从结果看,运动令人更加健康是机体代谢改善的外在表现,究其内因,与控制这些代谢过程的蛋白干系颇深,因此有科学家进一步向前追溯:运动会直接影响到表达上述蛋白的基因。【运动,或许改变了我们的基因表达。 图片来源 precisionnutrition.com】改变即刻发生 经由这一线索出发,越来越多的证据正在浮出水面。 2012年,《Cell Metabolism》杂志刊登了一项瑞典卡罗林斯卡大学医院的学者兹尔罗斯及其同事开展的一项研究。他们发现,运动在极早期就可影响到肌肉细胞的DNA。 在该研究中,兹尔罗斯招募了14名平日并不经常锻炼身体的健康青年男女。要求他们骑行健身脚踏车,达到一定的运动量后方可停下。在骑行前后,研究人员采集了受试者四头肌处的少量样本用于分析。当然,样本采集全程在局麻条件下进行,并不会给受试者带来痛苦。 借助这些运动前后活组织样本的对比,兹尔罗斯对一系列相关基因的表达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运动后,相当多的基因被打开并激活。在这些基因的作用下,肌肉细胞释放了大量的酶类,从而让肌肉细胞燃烧热量,并获得运动所需的能量。 兹尔罗斯发现,这些基因之所以能被激活,是因为DNA甲基化的程度减弱了。甲基化是一个表观遗传学名词,初听蛮拗口,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基因的开关,亦即如果DNA的特定区段附着有这个结构,那么相应的基因表达就会减弱甚至关闭。 在某种机制作用下,运动使得DNA上的甲基得以移除,而且兹尔罗斯发现,运动强度越大,甲基移除的效果越好。受试者曾在一周内进行过两次强度不同的骑行锻炼,一次强度达到其运动极限的40%,另一次则为80%,而后分别提取肌肉活组织样本进行分析,结果不出所料,运动更大,甲基化的程度就更弱。 亦有长期影响 人的基因组无比的复杂与动态,外界条件发生改变时,在特定生物化学信号的作用下,会发生相应变化加以因应。现在我们知道,短期运动对DNA甲基化即有影响,那么,长期坚持运动的话,甲基化水平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兹尔罗斯的同事林德霍姆继续进行了探索。这项研究刊载在2014年12月号的《Epigenetics》上。 研究伊始,林德霍姆同样招募了23名健康的青年男女,仍打算利用兹尔罗斯的研究方案。不过,根据此前的一些发现,当人们暴露于污染物之中或食用了某些食物时,人体一些基因的甲基化水平同样会发生改变。由于此次观察的目标是长期运动对DNA甲基化的影响,因此必须排除其他混杂因素的影响,以厘清到底哪些改变是由运动所致。 林德霍姆想到了一个巧妙的方法来克服这一困难:要求受试者单腿骑行,也就是说要指定一条腿锻炼,另一条腿休息。这样一来,一条腿可被视为实验组,另一条则是对照组。锻炼频率为每周4次,每次45分钟,共需持续3个月,而后分别进行活检。 毫不意外,受到锻炼的腿变得更加强壮,但DNA层面发生的改变却更加有趣。林德霍姆检测了受试者肌肉细胞基因组上逾5000个位点,除了发现有些基因的甲基化程度减弱外,还找到有些基因出现了增强。这其中,有很多基因在人体的能量代谢,胰岛素反应以及炎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锻炼终止,那么DNA甲基化是否会重回原状呢,对于这个问题,林德霍姆打算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加以解决。她提到,尽管运动如何改善人体的健康,目前仍没有明晰的答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先跑起来再说。参考文献
新品
2015.07.28
淋巴瘤精准治疗潜在靶点发现
《中国科学报》记者黄辛 通讯员丁燕敏2015-07-27 第1版 要闻文章来自科学网 北京方程佰金科技有限公司再次编辑排版!尊重作者,转载请注明。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协同创新中心的上海血液学研究所联合我国血液/肿瘤临床多中心研究机构的17家医院,对/T细胞淋巴瘤(NKTCL)这一具有独特地域性和临床特征的血液肿瘤进行了基因组学、分子病理学和临床预后相关性研究,取得了精准医学领域的突破性成果。相关研究7月20日在《自然—遗传学》杂志上发表。自然杀伤/T细胞淋巴瘤是一种恶性增殖的特殊类型淋巴瘤。该病在亚洲地区人群中相对高发,发病凶险,预后很差。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娟、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和系统生物医学协同创新中心教授赵维莅带领研究团队,利用第二代测序技术对25例NKTCL进行了全外显子组测序,解读了基因组中基因编码区域的信息,并通过多中心研究机构平台,在扩大的80例NKTCL患者样本中进行了全面验证。研究结果发现,细胞中调控RNA结构和功能的一个重要基因在NKTCL中存在高频突变,抑癌基因TP53突变频率次之,两种基因突变率相加占全部基因突变的32.4%,且两者的致病机理有高度相关性。蛋白和细胞功能研究显示,一种基因突变是患者预后不良的分子标志,同时,结合TP53突变以及淋巴瘤国际预后指数情况,可进一步将NKTCL患者分为低危组、中危组及高危组三组。这是迄今为止NKTCL最全面系统的基因组学图谱,也是对相关突变基因致病原理及其临床意义进行的深入系统阐述。专家认为,这些结果使NKTCL临床预后判断分层更为清晰和严谨,并为该病的分层精准治疗提供潜在的靶点。
标准
2015.07.27
医学实验领域流行囤积数据,还能不能好好做研究了?
文章来自煎蛋网王丢兜,尊重他人劳动成果,转载请务必注明!北京方程生物重新排版2015.07.27同行评审和重复检验是科学方法的关键,但在医学实验领域,制药公司的不肯放手加上科学家们害怕自己的人为错误遭受耻笑,意味着我们赖以做出生死攸关决定的原始数据被常规性地保留,意味着错误会成年累月潜伏不被发现——有时候就是永远。以“干死制药厂”著称的Ben·Goldacre撰写文章,试图解开导致临床实验数据保密现象的错综复杂的网络,表达了对数据进行独立审核的急迫。对立性同行评审过程中,你朋友会指出你的错误而你的敌人直接叫你白痴。这很令人受伤——而且它正变得如此不常见,以至于媒体都把研究中的人为错误当成丑闻来报道,而不是以它常规现象的本来面目。这就变成了恶性循环:研究者们害怕发表数据,使得检出错误更为罕见。而这种罕见性又会把被发现的错误变成丑闻。丑闻使研究者们更不愿意发表。Ben对此有一个精彩的比喻:评估他汀类药物疗效的最佳方法是组合所有试验的原始数据。本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社论解释他们已经向32个主要他汀类药物试验发出了原始病人数据的请求。虽然他们用电话和电邮进行跟进,只有7家团队屈尊回应。进行一项试验,然后拒绝让任何人看到数据,就好像声称你发射了飞船去冥王星,但就是不上图给人看。这是可笑的。但制药公司和研究者们保密数据的理由比这也几乎合理不了多少。有时候,他们玩弄恐吓和权威。他们会说,那些白痴们怎么整?那些反对疫苗阴谋论者,以及喜欢他们的记者们:他们难道不会在好好的数据里挑骨头,利用这些信息惹是生非么?好吧,这星期NASA飞了一艘船掠过冥王星,真相党果然适时出现说这都是假的。白痴记者还报道了。然后……天也没塌下来啊,NASA没被收走拨款。这些指控被热心博主们一一戳破。然后每个人还都转发了巴兹·奥尔德林一记老拳打在一个阴谋论者脸上的视频。
百态
2015.07.27
生物实验室培育出来的“假肢”
文章来自果壳网,方程佰金公司再次编辑作者Andy Coghlan 本文主要编译自World's first biolimb: Rat forelimb grown in the lab,部分段落根据原论文进行了一些增补。文中图片来源:B J Jank, Ott Laboratory。这看起来像是一截被砍断的老鼠爪子,不过正确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加振奋人心:这截大鼠前肢其实是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中用活体细胞培育出来的人工产物。尽管尚不完美,但这一技术可能会在未来帮助人们研制出真正具有生物学功能的义肢。 “我们目前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前臂与手掌上,用于模型系统的建立与基本原理的验证。”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的哈拉尔德·奥特(Harald Ott)是培植这条大鼠前肢的主要功臣之一。“不过,同样的技术还可应用于腿和胳膊等其他四肢部位。”“这就像现实版的科幻小说。”佛蒙特大学医学院的丹尼尔·维斯(Daniel Weiss)如是说,他正在研究肺脏的再生。“这是一项激动人心的新技术,但如何制作一条功能齐备的肢体将是一大挑战。”许多接受了截肢手术的患者身上安装的义肢在外观上毫无问题,但却无法像真正的四肢那样发挥功用。现在,市面上又出现了一些利用仿生学的人工义肢,它们可以发挥功能,但不自然的外观依旧是个硬伤。手部移植手术是另外一种解决方案,目前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为了防止身体出现排异反应,接受移植的患者也需要终生服用免疫抑制药物。而生物肢体(biolimb)一旦成功,以上诸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这种肢体由患者自身的细胞“培植”而成,因此不需要免疫抑制药物的辅助,而且它在外观和运动功能上都将与自然状态的肢体十分接近。“这是对生物肢体培育的初次尝试,而且据我所知,目前尚无其他技术培养的复合组织能够达到我们的复杂度。”奥特说。如何做出一条前肢?制作这条大鼠前肢的技术叫做“decel/recel”(分别是decellularization和recellularization的缩写,意为“脱细胞化”与“再细胞化”),之前在实验室中,这种技术已经被用于研制人造心脏、肺脏和肾脏。利用该技术制作的一些简单器官——例如气管和声带——已经被用于移植手术,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不过,它也遭到了一些非议。人造器官的第一步是“脱细胞化”:供体的器官/肢体经过去垢剂处理,剥离了全部的软组织,仅留下由惰性的胶原蛋白构成的器官“支架”,从而完好地保留它们原有的复杂结构。在此次培植大鼠前肢的实验里,血管、肌腱、肌肉和骨骼处的胶原蛋白结构在此步操作之后被存留了下来。第二步就是“再细胞化”,这时要将接受移植个体的细胞“种”在“器官支架”上,然后将它们放在生物反应器中培养,让新的组织细胞依附支架生长起来,最终使器官重新恢复“有血有肉”的状态。最终,新的器官上不会留下任何带有供体细胞特征的软组织,所以它也不会被到受体的免疫组织识别为“异己”。这样一来,排异反应就可以避免了。同样是利用脱去细胞再培养的方法,造出一条前臂可比培养气管难得多,因为前者需要培育更多种类的细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奥特首先将脱细胞后的大鼠前肢“骨架”置于生物反应器当中,并利用一套人工循环设备为其提供养分、氧气以及电刺激。随后,他将人类内皮细胞注入血管的胶原支架,1个小时之后,内皮细胞重新附着在血管表面。这一步非常关键,他说,因为这样能使新长出来的血管更加结实,而不会在内有液体循环的情况下出现破裂。接下来,他将小鼠成肌细胞、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以及人类内皮细胞混合在一起,注入前肢支架中原本被肌肉组织占领的空位。2~3周后,血管和肌肉的重建完成。最后,奥特给前肢实施了皮肤移植手术,终于大功告成。不过,这条前肢的肌肉能用吗?为了验证这一点,研究团队利用电脉冲刺激肌肉,发现大鼠爪子真的会做出抓握动作,而且肌肉的强制性张力达到了新生大鼠肌肉的80%。“这说明我们能实现手掌的弯曲与伸展。”奥特说。他们还为若干只大鼠进行了移植手术,实际检测了这种生物肢体的功效。血管连接完成后,受体大鼠的血液顺利流入了人造前肢的血管,并且能记录到血流的脉动。不过,他们并没有在活体大鼠上测试肌肉运动功能或排异反应。 前路漫漫奥特表示,尽管他们已经完成了近百条大鼠前肢的脱细胞化,又给其中至少一半的支架“种”上了新的细胞,但目前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首先,他们需要在肢体里种上组成硬骨、软骨等其他组织的细胞,观察这些细胞能否再生。下一步,他们必须证明神经系统也能完成重建。前人的手部移植手术结果表明,受体的神经组织能够延伸并穿入新接上的手掌,最终实现对新器官的控制。而人工培植的生物肢体是否也能做到这一步,还有待进一步实验验证。除此之外,奥特和同事们还在论文中展示了灵长类动物前臂成功被脱细胞化(见下图)的成果。目前,他的团队已经开始在灵长类动物的“支架”上培育人类血管细胞,这是通往人类生物肢体技术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在大鼠试验用人类成肌细胞替代小鼠成肌细胞并观察效果。不过,奥特指出,大量的后续工作必不可少,在满足人体测试要求的生物肢体出现之前,我们至少还需要等上10年。脱细胞处理的灵长类肢体。“这是一次值得瞩目的进步,而且具备坚实的科学基础,不过,哈拉尔德的团队还需要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难题。”宾夕法尼亚州匹茨堡大学的史蒂芬﹒巴蒂拉克(Steven Badylak)评论说,他曾经在猪肌肉组织制成的支架上进行移植体培育,并在13名病人当中成功实现了腿部受损肌肉的再生。“在所有这些问题当中,血液循环可能是最棘手的一个,而且你必须确保内皮细胞能覆盖到最细小的毛细血管,这样它们才不会塌陷并导致血栓,”他说道,“不过,将已知的生物学基本原理投入实际应用其实是一个工程问题,工程师们就是这么做的。”其他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更多批评意见。“对于手这样的复杂器官而言,其中的组织和结构实在太多了,因此这种方法肯定是不现实的。”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奥斯卡﹒埃兹曼(Oskar Aszmann)说,他曾经发明了一种可以用“意念”控制的仿生手。“而且,要想让一只手实现有意义的功能,就必须让它长满成千上万的神经,这在目前依旧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难关。所以,尽管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但它在当前只能停留在基础研究阶段,而无法进入临床实践。”奥特设想,将来人类的器官捐赠计划或许也将囊括四肢捐赠。用于再生血管的细胞可以从受体的小血管中获得,而肌肉细胞则可从大腿等部位的大型肌肉中取得。“如果提取大约5克(的肌肉组织),就能从中培养出人类骨骼肌成肌细胞。”仅仅在美国就有150万的截肢者,因此此项肢体再生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奥特如是说。“目前,如果你失去了胳膊腿,或是因为癌症治疗、烧伤等缘故损伤了部分软组织,能供你选择的治疗方案是很有限的。”(编辑:窗敲雨)
新品
2015.07.24
科学作假-最大的科学造假者落网了
科学界最大造假者落网记Adam Marcus、Ivan Oransky 发表在果壳网北京方程生物重新编辑格式,内容无改变!(Cuscoasimo /译 )2000年4月,《麻醉与镇痛(Anesthesia & Analgesia)》杂志刊发了一封致编辑函,彼得·克兰克(Peter Kranke)与2位同事所写的这封信里满含讽刺。这3位麻醉学者把矛头指向了一篇日本同行发表的文章,作者是藤井善隆(Yoshitaka Fujii)。他们认为,藤井所发文章中有关一种手术后恶心呕吐预防药物的数据“好看得不可思议(incredibly nice)”。日本研究者藤井善隆 图片来源:arstechnica.com在科学行话里,说研究结果“好看得不可思议”可不是一种赞赏——这等于指责研究者漫不经心,甚至是伪造结果,可是《麻醉与镇痛》杂志没注意到其中的警告意味,而是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在致编者函之后,《麻醉与镇痛》杂志附上了藤井的解释;他问道:“究竟什么样的证明才能算充分证据?”换句话说就是:“你们不信我?那就不信好了。”此后,《麻醉与镇痛》杂志还继续发表了藤井的其他11份论文。德国维尔茨堡大学(University of Würzburg)的克里斯蒂安·阿普费尔(Christian Apfel)是致编者函的作者之一。他曾前往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提请该机构注意他与同事发现的问题。不过,他从来没得到任何回复。也许是认识到自己的好运气来源于审核的宽松,藤井自2005年前后就几乎不再发表麻醉学文献。他转向了眼科学和耳鼻喉学。在这些领域里,他的那些侥幸之作不太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截至2011年,他已经发表了200多项研究成果,这对于他所在的领域算得上是多产了。2011年12月,《麻醉学杂志》(Journal of Anesthesia)发表了藤井的一篇论文,这是他的最后一篇论文。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一个事实变得日趋明显,藤井的许多(实际上是绝大多数)研究成果是伪造的。他是当今单个作者被撤稿记录的保持者,总数高达惊人的183篇,约占1980年至2011年间全部撤稿数的7%。藤井不仅是个从声名卓著到声名狼藉的典型,他的经历还开启了学术出版的新纪元:一个属于检测学术欺诈的统计工具,以及乐意使用这些工具的学术“警察”的时代。在从2009年起担任《麻醉》(Anaesthesia)期刊的总编辑前,史蒂夫·延蒂斯(Steve Yentis)就有着相当深厚的科研伦理背景。他担任过一个麻醉学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及主席,甚至利用业余时间取得了医学伦理学硕士学位。此外,延蒂斯还为出版伦理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COPE,一个位于英国的国际组织,致力于修订学术出版标准)工作。但他在履新后还是没有“预感到天快要塌下来了”。与十年前的《麻醉与镇痛》杂志一样,《麻醉》在2010年刊登了一篇关于藤井论文的编辑意见。意见作者们不相信藤井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号召全学科对藤井所发论文进行审核并,清除造假的结果。后来,延蒂斯在一篇题为《谎言、弥天大谎和统计学》的文章中说,这篇由他约稿发表的编辑意见引来了洪水般的来信,其中一位来信读者 表示“为这种研究者在论文中歪曲证据基础的情况感到惋惜”,并强烈要求麻醉学期刊杂志编辑对此有所行动。这封信的作者是英国麻醉医生约翰·卡莱尔(John Carlisle)。在某种意义上,这篇编辑意见的刊发恰逢其时。在此之前,麻醉学领域接连了遭受两次重大打击,刚开始慢慢恢复。第一次打击来自一名美国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疼痛医师斯科特·鲁本(Scott Reuben),他伪造了临床试验数据。不到一年之后,一位多产的德国研究人员乔基姆·博尔特(Joachim Boldt)就制造了第二次打击:人们发现他篡改了研究论文,并且还有其他违反学术伦理的行为,这些不端行为总共导致博尔特被撤稿90篇。斯科特·鲁本(左)和乔基姆·博尔特(右) 图片来源:tovima.gr 与www.cbsnews.com如果事情看起来好得让人难以置信,那么数学会告诉你真相 《麻醉》发表过博尔特的6篇论文,这使延蒂斯感觉有些难堪。因此,当看到卡莱尔的来信后,他发现了机会。延蒂斯明确告诉卡莱尔,他不能只当键盘侠, “我反过来要求写信人对藤井的研究进行分析。” 卡莱尔承认自己当时既没有统计学专长,也不是特别有名的麻醉学家,说的话在同行中间也没有什么分量。但他的结论十分简单,也无法忽视:藤井的研究数据基本上不可能是从一组真实实验中获得的。临床医学中的最佳证据来自随机对照试验,本质上来说,就是靠统计学把“偶然的随机反应”和“药物或其他治疗手段的真实效果”区分开来。卡莱尔解释说:“通常来说,实验里有治疗组和安慰剂组,分析的是接受治疗后和接受安慰剂后的两组数据;而我所做的不寻常之事就是分析在接受治疗之前或给予安慰剂之前,这两组变量之间的差异(比如说体重),并计算出这些差异小于,而不是大于观察结果的概率有多大。”藤井善隆在1991年至2011年间曾进行过 168次满足“黄金标准”的临床试验(这使得他每年发表的论文数达到令人瞩目的8篇)。卡莱尔将藤井的实验结果与其他研究人员先前取得的数据,以及随机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并查看了从研究开始时病人的身高、血压,到藤井所测试的药物发生副作用的频率等各项因素。利用这些方法,卡莱尔在他2012年发表于《麻醉》杂志的论文中得出结论,藤井善隆在实验中获得这些研究结果的概率约在10-33这个数量级,一个小得可怜的数字。在这篇论文中,卡莱尔用晦涩的术语解释道,藤井的数据中存在“不正常的模式”,说明“这些数据偏离随机样本的程度足以将它们排除在证据基础外”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事情看起来好得难以置信,那么数学可能会告诉你那确实不可置信。卡莱尔的结论与那些在2000年呼吁对藤井进行审核的麻醉学家所持观点很像——只是这次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卡莱尔的研究结果发表后不久,日本的一项研究结论显示,藤井善隆发表的212篇论文中仅有3篇包含明确可靠的数据,38篇论文无法被确定是否为欺诈,171篇论文最终被认定完全伪造。这份日本调查报告总结道:“这就像是他坐在书桌前,写了一部关于自己的研究假说的小说。” “警察”:《麻醉》(Anaesthesia)总编辑史蒂夫·延蒂斯(Steve Yentis),曾要求一位读者开展对藤井善隆研究论文的统计学分析。 图片来源:nautil.us卡莱尔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麻醉,甚至不仅适用于和人有关的科学。卡莱尔说:“我用的方法可应用于任何事物、植物、动物或矿物等。它只要求把人、植物或事物随机分成不同的组。”这对于其他学术刊物来说也“相当容易”实行。至少有一位期刊编辑同意卡莱尔的说法。斯坦福大学麻醉学家、《麻醉与镇痛》现任总编辑史蒂文·谢弗(Steven Shafer)说:“虽然它还在发展,但是约翰·卡莱尔的基本方法已经被作为一种检测研究欺诈的工具推广开来。”谢弗、延蒂斯以及其他人都在为此而努力。卡莱尔计划最近发表一种改进后的方法。谢弗表示,他们的目标之一就是使这个过程自动化。谢弗表示,他曾经亲自运用卡莱尔的方法鉴别出一篇2012年投给《麻醉与镇痛》的欺诈性论文。谢弗拒收了此论文,后来得知它被投递给了其他期刊。谢弗说:“同一篇论文,数据重新编过了!我在拒稿信中暗示那是一篇欺诈性论文,论文作者看到之后就编造了新的数据。”谢弗与同事向该论文作者所在院系负责人写了一封提示信,对方回复说:“这些人以后不会再搞研究了。”而且,这种方法也不仅可以用于鉴别欺诈者。卡莱尔表示,科克伦协作组织(Cochrane Collaboration,一家开展医学文献审核与元分析的英国组织)等团体可以利用此技术检查任意合作成果的可靠性。这类元分析会把特定干预手段(例如药物或手术等)的许多研究结果汇集起来,因此被视为制定治疗规范的强大循证工具。然而,如果各项研究的数据基础有问题,那结果就是“输入的是垃圾,输出的还是垃圾”,毫无用处。不过,这种方法要求期刊编辑参与其中——而目前,许多编辑并不愿意。有人认为有理由不对论文进行修正。而作者则从自身利益出发,宣称自己是“莫须有迫害”的牺牲者。更常见的情况是,允许对已发表论文匿名评论的网站(如PubPeer.com)上出现大量批评声音之后,媒体报道跟进,人们才会进一步采取行动。例如在2009年,布鲁斯·艾姆斯(Bruce Ames)——因名字被用来命名致癌物测试而出名的那位——与同事一起开展了一项与卡莱尔研究类似的分析研究。研究的对象是3篇由帕拉尼纳森·瓦莱拉克什米(Palaninathan Varalakshmi)所领导团队撰写的论文。与后来卡莱尔的研究成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次调查中,3位研究者回击了,他们声称,艾姆斯的方法是“不公平的”,是对因果关系和相关性的混用。瓦莱拉克什米的编辑同意他们的看法。直至今天,在发表过这些受指控的研究者的论文的期刊中,还没有任何一家对他们的论文采取任何行动。可悲的是,这种情形才是学术欺诈调查的典型结论。难于对欺诈者追责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学术出版本身。延蒂斯认为,学术出版“一直依赖于人,而不是体系;同行评审过程有其自身的优缺点,但欺诈检查真的不是它的强项”。发表的基础是信任,而就算能获取原始数据,同行评审者也往往会匆忙略过。例如《自然》(Nature)执行编辑维罗妮卡·基尔默(Veronique Kiermer)就表示,该杂志要求作者“采用适当的统计学测试,并着重说明数据是否符合统计学测试的假设”。她认为,编辑“在评价论文时,应当考虑上述要求,而不需要系统地检查论文涉及的全部数据的分布。”类似地,同行评审者也并不被要求检查数据集的统计情况。去年,《自然》发生了一次惨痛的干细胞论文撤稿事件,并导致一位主要研究人员自杀。但他们依旧认为:“我们和评审者不可能发现那些严重削弱论文质量的问题所在。”该杂志社表示,他们进行了出版后同行评审,以及制度性调查。《自然》刊登的另一篇编辑意见中写道,查得太严会产生真正的问题。期刊杂志社“可能发现自己会仅仅因为要求撤稿这个行为就惹上官司,更别说在撤稿声明中提到学术不端了。”《自然》或许仍然满足于将繁重的审查工作留给学术机构,但延蒂斯已经得到了教训。虽然在他2010年授权发表的那篇社论中,藤井善隆论文中的问题引起了读者关注,但是他也几乎忽略了那篇社论传达的信息。直到来来往往好几轮通信后(包括最终破案者卡莱尔写给他的信),他才行动起来,直到2012年才刊出了那篇决定性的分析文章。延蒂斯说:“如果现在的编辑意见中出现那样的指控,我绝不会再让它从身边溜走。”(校对:Stellasun;编辑:游识猷)
新品
2015.07.24
肝功能衰竭甚至肝癌是怎么被吃出来的?
食物也能摧毁肝脏:我们是怎样吃出肝功能衰竭甚至肝癌的?文章摘自果壳网,作者亚得里亚海上的猪北京方程生物(Mitch Leslie /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天,一个病人来到了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医学中心,当他走进乔·拉文(Joel Lavine)的办公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病得有多厉害。这是一个病态的胖子,身上长着一种称为“黑棘皮病”的褐斑,从脖颈后部一直延伸到腋窝,这说明他的身体多半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也就是说,他的细胞已经无法对控制血糖的胰岛素产生正常反应了。 活检显示,这名病人的肝脏已经遭到了相当的破坏:大量脂肪挤进细胞,压扁了细胞核及其他细胞器。瘢痕组织驱逐健康细胞,造成了肝硬化。病人长着一名中年酗酒者才有的肝脏,而实际上,他只是个8岁的儿童。在拉文这个儿童肝病学家看来,眼前的这名男孩显然是患上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简称NASH)。这种疾病一般与肥胖有关,病人的肝脏内积聚了过量脂肪,而且正如它的名字所显示,这些脂肪并非来自饮酒过量;虽然过量饮酒也会引起严重的脂肪肝。因为NASH能够摧毁肝脏,病人可能需要肝脏移植,也许还会死去。拉文九十年代初曾在波士顿儿童医院工作,当时他就遇到过几例NASH的儿童患者,但是到了圣迭戈,他发现情况完全不同,这里有庞大的拉美裔人群,NASH在儿童中间“堪称猖獗”。每个礼拜都有十几个怀疑得了这种疾病的孩子到他的办公室来求诊。“很明显,这已经算得上是一种传染病了。”现在,拉文已经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内科与外科学院工作。这种“传染病”已扩散到了全美国,这是我们的肝脏为高热量饮食和静态生活方式付出的代价。在美国,即使不酗酒的人中间,也有大约有两到三成人的肝脏里携带了过量脂肪,而这就是NASH的先兆。眼下,NASH甚至开始在一些看似不可能的地方冒了出来,比如印度农村。巴黎比提耶-萨尔贝提耶尔医院的肝病学家弗拉德·拉特祖(Vlad Ratziu)指出:“这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医生和研究者都表示这个问题值得担忧,因为肝脏内的脂肪积聚虽说以良性居多,但是在这些肝脏堆积了脂肪的人中间,有大约30%会发展成NASH,而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肝功能衰竭、肝癌和死亡。对于NASH,现在无药可治;对于许多患者,移植一只新的肝脏是唯一的办法。眼下NASH已经是肝脏移植的第二大原因,而据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那伽·查拉桑尼(Naga Chalasani)的说法,到2020年它就可能升上第一,因为到了那时,丙型肝炎会得到新一代抗病毒药物的控制,它将不再是肝功能衰竭的最大原因,由此产生的移植需求也会下降,并为NASH取代。与此同时,NASH的发展与恶化的轨迹也变得清晰了起来,这使得制药公司跃跃欲试。眼下已经有20多种潜在的药物正处在开发的某一个阶段,有几种还在前期的临床试验中取得了佳绩。尤其是一种称为“奥贝胆酸”(obeticholic acid)的,最近使研究者备受鼓舞,它能减轻NASH的一个严重后果,即肝脏瘢痕(liver scarring)。拉文表示,现在正是NASH治疗史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拉特祖也预测:“五年之后,至少会有一种疗法获得批准。”不喝酒,不代表一定不会得肝病脂肪肝的发展过程:一只健康的肝脏(1),堆积起了脂肪(2),继而发展成NASH,具体的表现有炎症(3)和细胞肿胀(4),有时还会产生瘢痕(5)。图片来源:Science过去几十年里,NASH始终没有得到认可,这主要是因为医生们老是把它和酒精性脂肪肝炎、也就是ASH混为一谈。ASH的症状同样是脂肪在肝脏内淤积,只不过它是由酗酒引起的。弗吉尼亚大学夏洛茨维尔分校的肝病学家斯蒂芬·考德威尔(Stephen Caldwell)说,有的病人肝脏里脂肪淤积却否认酗酒,但医生还是咬定他们在暗中狂饮。在那些医生看来,“如果你有肝病,你就一定酗酒。”直到1980年,梅奥诊所(Mayo Clinic)的尤根·路德维希(Jurgen Ludwig)和同事才在“ASH”前面加上了“N”,以此描述一群肝脏被脂肪损坏、却没有酗酒习惯的病人。拉文介绍说,在那以后又发现的大量患有NASH的儿童,这才彻底扫清了医生们尚存的一点怀疑,使他们相信这种疾病确实与酒精无关。 到今天,肝脏里的多余脂肪已经很容易用成像技术发现,但是要确定有多少人患上了NASH这种严重的脂肪肝,就比较棘手了。德州布鲁克陆军医学中心的肠胃病学家斯蒂芬·哈里森(Stephen Harrison)指出:“要确诊患者是否得了NASH,唯一的办法就是肝脏活检。”他说,这种检查只要“在皮肤上划道口子”,无需开膛破肚,但病人还是常常拒绝,这使得NASH的普遍性很难确定。照研究者的估计,它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在2%到5%之间。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分子生物学家杰伊·霍顿(Jay Horton)指出,归根到底,脂肪肝是一种“热量过多导致的疾病”。人体吸收的热量多于消耗的热量,就会引起一连串复杂变化,并最终改变肝脏的特征。许多从饮食中获得的脂肪酸会进入血流、抵达肝脏,再由肝脏指挥,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正如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营养生理学家伊丽莎白·帕克斯(Elizabeth Parks)所说,“肝脏是人体的交通警察”,生产脂肪的原料怎么分配,全靠它的引导。肝脏本身很少储存脂肪。帕克斯表示,一个身体健康的70公斤男性,他体内的脂肪大约是14公斤,其中驻留肝脏的只有125克。“这个数量实在很小,而且肝脏还有许多办法摆脱它们。”她说。但是在有些人身上,肝脏却变成了容器,开始囤积一种叫做“甘油三酯”的脂肪变体。有时甘油三酯会大量堆积,而这时的肝脏,用拉文的话来说,“就像一块黄油”。除了食物中的脂肪酸,研究者还发现了肝脏脂肪的另两个来源。一是肝脏之外有一种“脂肪细胞”(adipocytes),它们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内部的脂肪,而这些脂肪最后也会抵达肝脏。二是肝脏本身也会合成一些脂肪。这三个来源都会加重脂肪肝。最近,帕克斯和她的团队又展示了肝脏是如何给自身制造灾难的。她们让志愿者吃下用放射性化合物做了标记的食物,以此追踪自由脂肪酸的合成,而自由脂肪酸正是甘油三酯出现的前兆。结果发现,患有脂肪肝的人,在肝脏中制造的自由脂肪酸比健康人群多三倍。这个结果发表在去年的《肠胃学》(Gastroenterology)杂志上。查拉桑尼认为,在诸多可能导致肝脏内淤积脂肪的代谢异常当中,胰岛素抵抗是一个关键。食物中的营养过剩,往往会导致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降低,由此使得脂肪通过几种方式在肝脏内堆积。比如,胰岛素在正常情况下会促使脂肪细胞停止分泌脂肪酸。然而帕克及其同事却在去年的研究中发现,产生了胰岛素抵抗的脂肪细胞会继续往血液中注射脂肪酸。一般来说,肝脏能够输出甘油三酯,从而摆脱一部分脂肪,然而胰岛素抵抗却会使它合成更多甘油三酯、使原来的排放机制不堪重负。 还有一些因素也可能引起脂肪在肝脏中的自然增长,像是肠道中的微生物,或者遗传基因。举例来说,如果代谢基因PNPLA3发生了特定的变异,就会增加脂肪肝的危险。脂肪肝患者的肝脏里堆积了过量的脂肪,下面五个因素决定了到底过量多少:①饮食,我们吃下的脂肪可能移动到肝脏,有一些会在那里储存起来。②脂肪细胞,这些细胞能够储存脂肪,也会释放脂肪酸,这些脂肪酸可能移动到肝脏。③肝脏制造的脂肪,脂肪肝患者的肝脏会制造更多脂肪酸。④低密度脂蛋白(VLDL),靠着制造这些微粒,肝脏能摆脱一些多余的脂肪(但还不够)。⑤胰岛素抵抗,这种疾病使得脂肪细胞喷出脂肪、肝脏制造脂肪。 图片来源:Science当脂肪堆积进展到脂肪肝炎脂肪堆积常常带来许多健康问题,比如肥胖症和糖尿病,不过哈里森指出,肝脏的这些多余负担也未必会致人死亡,患者很有可能“带着脂肪肝活到老年。”然而,对于病情发展到NASH的人,情况就不那么妙了。他们中有25%会出现肝硬化的症状,并因此失去肝功能。和病情较为温和的脂肪肝病人相比,NASH患者往往表现出两种特殊的病状:一,随着白细胞渗入肝脏,肝脏的炎症更加严重;二,肝脏中数量最多的肝实质细胞发生“气球样变”(ballooning),肿胀到原来的两倍大,而这就是肝实质细胞凋亡的前兆。这两个现象继续发展,就会引出另一个险恶的症状:纤维化,也就是富含蛋白胶原的瘢痕组织大量生长。随着瘢痕的扩散,肝脏的各个区域被接连占据,健康的细胞也越来越少,这有时就会导致肝功能衰竭。肝硬化还会引发肝癌,不过其中的病变规律研究者还没有弄清。 肝脏是怎样一步步被摧毁的。脂肪肝可以通过饮食控制和运动来“逆转”成健康肝,NASH也有希望逆转回脂肪肝。但一旦发展到肝硬化,就无法再逆转了。图片来源:www.sec.gov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肝病学家罗希特·隆巴(Rohit Loomba)指出,现在最大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三分之一的脂肪肝患者会发展出NASH,还没有答案。有的科学家认为,或许脂肪本身就对肝脏细胞有毒,也有一些证据显示炎症和氧化应激才是罪魁祸首。瘢痕组织是否会在布满脂肪的肝脏中扩散,或许还要看肝脏的自我修复能力。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肝病学家安娜·梅·迪尔(Anna Mae Diehl)和同事发现,NASH患者的肝脏修复功能都出现了差错,原因是一条分子信号通路过分活跃,而正常情况下,这条通路只在个体发育阶段比较活跃。在胚胎中,有一种“刺猬蛋白”同其他蛋白一起塑造了脑、肾脏、肠道和其他身体器官。等到个体长大成人,这条通道就会在肝脏中关闭,但是如果肝脏受到损伤,它又会重新开启。在它的刺激之下,某些肝脏细胞就转变成了制造瘢痕的细胞。迪尔和她的同事认为,在NASH患者体内,那些发生气球样变的肝实质细胞可能就祸首。她们在2011年的《病理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athology)撰文指出,肿胀的肝实质细胞会制造大量蛋白、打开刺猬通路。眼下医生对NASH患者还没有什么治疗办法,只是建议他们少吃、多运动。如果一个患者的情况恶化到了肝脏开始衰竭,或许他就要接受移植手术了。但是考德威尔表示,目前看来,“要挽救一个病得很重的人,手段还是有限。”这个严峻的现实或许很快就会改变。许多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都已经启动了NASH药物的研发工作,吸引它们的是对长期药物的巨大潜在需求——有人估计,这类药物的市场将达到每年350亿美元。研究者们已经试验、或者希望试验的药物包括维生素E、专治糖尿病的匹格列酮(pioglitazone)、以及大量新的合成物质。“有趣的是,它们的作用模式几乎各不相同。”拉特祖说。有一种药物称为“aramchol”,它混合了一种合成脂肪酸和胆汁酸,目前正处于二期临床试验,以确定它能减少多少肝脏中淤积的脂肪。还有一种“cenicriviroc”,同样处于二期试验,它起初是作为抗病毒药物研发出来的,因为它能阻断免疫细胞上的若干受体分子,而这些分子正是病毒用来侵入细胞的通道。除此之外,它或许也能遏制肝脏的炎症和纤维化。 今年,至少有两种治疗NASH的药物可能开始三期试验,虽然其中的一种已经遭遇了挫折:此前,法国制药公司Genfit研发了一款称为GFT505的药物,它通过刺激分子受体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从而促使脂肪酸的分解,有274名NASH患者参与了二期临床试验。今年二月,公司宣布GFT505并没有在整体上减少这些患者肝脏内的脂肪或纤维含量,但其中最严重的几个病例确实有所改善。拉提祖表示,Genfit接下来还准备招募2500名NASH的严重患者,并对它们开展三期临床试验。好几个研究者都说,现在最有希望治疗NASH的药物是奥贝胆酸。肝脏会分泌胆汁酸以促进肠道吸收脂肪,从而促进脂肪的管理和糖分的代谢。奥贝胆酸则是一种改进的胆汁酸, 它能刺激一种细胞受体,从而提高细胞对于胰岛素的敏感性,并减少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去年十一月,圣路易斯大学医学院的布兰特·诺依施万德-泰特里(Brent Neuschwander-Tetri)报告了“FLINT试验”的成果。这是一项二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奥贝胆酸减少了NASH患者肝脏内的纤维组织,说明这种药物有可能逆转疾病的进程。拉文说道:“以前从来没有一种药物产生过这样的效果。”他本人就是这项试验指导委员会的一员。尽管如此,研究者(以及制药公司的投资人)依然相当谨慎。就像隆巴指出的那样,现在试验的药物当中,还没有一种能使50%以上的NASH患者获益。的确,奥贝胆酸是能降低纤维化,但与此同时,它也会增加低密度胆固醇(LDL cholesterol)的含量,而低密度胆固醇又会引起心血管疾病。查拉桑尼表示,这个副作用足以使人担忧,因为“那些病人的冠状动脉本来就很脆弱、易患心血管疾病。”不过,一项奥贝胆酸的三期临床试验还是会在今年夏天开始,2500名肝脏严重纤维化的患者将参与试验。对此,研究NASH的科学同行们第一次感到了希望。在诺依施万德-泰特里看来,NASH的预防和治疗,终于像是一个“可以够到的目标了”。(编辑:游识猷)
标准
2015.07.24
One Step Closer to an Ebola Virus Vaccine
Despite cautious optimism from the apparent recent slowing of the spread of Ebola virus disease (EVD) in some parts of West Africa,1 the remaining pockets of intense transmission and the recent incursion of the virus into Mali2 remind us that the battle for control is still on. This is no time to be complacent. The scale of this outbreak, in which every few days about the same number of cases accrue as occurred during the entire 3-month outbreak in Gulu, Uganda, in 2000–2001 — previously the largest outbreak on record — has prompted us to pull out all the stops, albeit after a slow start.3 Vaccines constitute a key, but still theoretical, weapon in our armamentarium against EVD. For some years, a number of promising vaccine candidates have been identified, with many more in development. The two leading candidates are vectored vaccines in which the Ebola virus glycoprotein is presented in a replication-incompetent chimpanzee adenovirus 3 (cAd3) or a replication-competent vesicular stomatitis virus (VSV). Both vaccines have shown 100% protection in nonhuman primates at 4 to 5 weeks after single doses were administered and have now been rushed into phase 1 trials in hopes that the promise of a vaccine to help stem the crisis in Africa can be more than theoretical.Ledgerwood and colleagues now present in the Journal the first results of the phase 1 VRC 207 trial, a nonrandomized, open-label trial of two dose levels of a cAd3-vectored bivalent vaccine against the two most virulent species of ebolavirus, Zaire and Sudan.4 They conclude that the vaccine was safe and immunogenic, inducing strong humoral and cell-mediated responses. Although the results of the trial are indeed promising, questions remain; both immunogenicity and reactogenicity were dose-dependent. The higher dose, which was required to generate the more vigorous immune response, was also associated with minor adverse effects in 70% of the participants, including one in whom a high fever (temperature, 39.9°C) developed, and with transient leukopenia in 20%. There were no major adverse effects, but the sample size (10 persons at each dose level) is too small to draw firm conclusions in this regard. Of particular concern is that the virus-specific CD8 T-cell response, which may be a key correlate of protection,5 was only 20% in the lower-dose group and 70% in the higher-dose group. Getting the dose right has relevance not only for ensuring individual protection and minimizing adverse effects, but also for stretching the vaccine supply to the maximum number of doses possible to combat the ongoing outbreak.Interpretation of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by Ledgerwood et al., as with all studies of filovirus vaccines, is hampered by a lack of knowledge regarding the specific correlates of immunity, although, as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e immune responses observed in their study involving human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associated with protection in efficacy studies in nonhuman primates.5 The matter is further complicated by a lack of standardization of stock viruses6 and the fact that, to achieve 100% mortality in control animals, and thus interpretable results, in studies in nonhuman primates, an extremely high challenge dose of virus (1000 plaque-forming units) is used, which is probably orders of magnitude higher than the inoculum that typically infects a human. Until the correlates of immunity are better understood,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whether the immune response shown at the lower dose in the study by Ledgerwood et al., which caused fewer side effects, is “good enough.” Will similar results be observed in West Africa, where malaria is holoendemic and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diminished immunogenicity with other vectored vaccines?7 At exactly what time point after vaccination is adequate immunity conferred? This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given the urgency of the situation in Africa. Will it be necessary to administer a booster with a modified vaccinia Ankara vaccine expressing the Ebola glycoprotein, which has been shown to increase the duration of immunity but would considerably complicate delivery?8 Results from ongoing phase 1 trials of a monovalent cAd3-EBO Zaire vaccine, which may be more immunogenic than a bivalent formation,9 as well as of the VSV-vectored vaccine, in various loc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Africa (outside the epidemic area for EVD) are due soon and may help answer these important questions.Perhaps one of the only silver linings of the EVD crisis that has shaken West Africa over the past year is that the event has pushed therapeutics and vaccines for EVD, which had previously been relatively stalled in development despite the promising results in nonhuman primates, into accelerated production and clinical trials. Assuming that the findings of Ledgerwood et al. are confirmed, especially in African populations, cAd3-EBO certainly warrants efficacy trials, but difficult decisions on the best dosage and trial design await. Can traditional phase 2 and 3 efficacy trials be performed in West Africa given the many ethical considerations, community expectations regarding the use of a placebo, and projected vaccine supply? Should the cAd3 and VSV vaccines be compared head-to-head? What should be the target population? And can it all be arranged in time for a human trial, or will we ultimately need to turn to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nimal Rule?10 The road is still long and there are many challenges, but we are nevertheless one step closer to a solution.http://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e1414305
厂商
2014.12.01
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也许能降低截肢风险
????英国新一期《自然—医学》杂志刊登的报告显示,一种与新血管生成有关的蛋白质或许可作为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标靶,降低此类疾病带来的外周动脉病变乃至截肢风险。外周动脉病变是导致腿部截肢的一种常见病因。患者血管内脂肪堆积,造成股动脉阻塞,腿部组织逐渐坏死,严重者必须截肢。英国诺丁汉大学和美国波士顿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重点考察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对此类疾病的影响。这种信号蛋白以两种形式存在,分别发挥两种作用,既可以促进新血管生长,也可以抑制其生长。研究发现,在外周动脉病变患者体内,这种蛋白全部以抑制血管生长的形式存在,导致堵塞的股动脉周围无法形成新的血管,以缓解血流不足造成的腿部组织缺血。研究人员给肥胖或患有糖尿病的实验鼠体内注入一种抗体,发现这样可有效阻止抑制血管生长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形成,使其发挥促进血管生长的作用。参与研究的诺丁汉大学教授戴维·贝茨说,这一研究为治疗外周动脉病变找到了新的标靶,通过操纵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改善腿部血液供给,降低组织坏死导致的截肢风险。研究人员下一步将考察上述抗体在人类患者中的作用。????
百态
2014.12.01